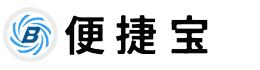


如果不是十年前去了杭州临安境内的大明山,我对苔藓的感知只停留在王维“生看苍苔色,欲上人衣来”的空灵,张九龄“皎洁青苔露,萧条黄叶风”的孤寂,宋之问“房中无俗物,林下有青苔”的超脱。在我心目中,青苔长在寂寥冷落处,可让文人雅士寄慨言志而已。
偶尔我会取厚质如毯的青苔装点阳台上的绿植,见青苔一铺,绿意浑然一体,心想它还算有点用处。而刘姥姥在潇湘馆的路上,被苍苔滑了脚,咕咚一声跌倒的情景记在心头,平日去单位上班,都要经过绿荫下一段青砖铺设的人行道,有时见砖缝间苔衣簇簇,砖面上苔点依稀,步子就迈得格外小心。

然而,我在茂林修竹的大明山遇到绚丽多姿的苔藓,颠覆了我对苔藓生物学层面的认知。大明山山岩累累,低矮的山体处长满苔藓,如同连绵不断的墙裙,它们向着高大的树木、巍峨的山体匍匐。我第一次见到薄荷绿、心叶卵状、叶片有卷边、似乎可以伸缩的苔藓,很像我在新加坡滨海湾花园看到的含羞草,一碰就羞答答地缩回去,我试着用指尖轻触苔藓的茎叶,它给我的指腹一个湿漉漉的吻;那些如少女麻花辫的翠绿青苔,在山腹恣意飘拂,像海浪轻拍岸湾,透着几分柔情蜜意;往山的深处去,苔藓愈发多样,粉、白、绿色彩相间的苔株,毫不逊色于春花秋果的魅力。它们株株直立,从岩石上稀疏的泥底拔地而立,叶片细长茂密,犹如烟花绽放于天空;最奇特的是婴儿手指般细嫩的粉色苔条,斗折蛇行,灼灼其华……
异彩纷呈的苔藓让我兴奋不已,我用手机拍下它们野趣横生的景象,留下如花似玉的倩影。我不禁责怪起随园主人袁枚,苔藓怎是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呢,分明就有牡丹的娇艳、槭枫的苍劲、兰草的幽洁。我俯身贴近眼前生意盎然、纤尘不染的苔藓,负氧离子澎湃于我的肺腑。
大明山的苔藓告诉我,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,是春风夏雨、秋露冬霜和斑驳的阳光孕育了它们亘古宁静、清冷绝艳、丰富而蓬勃的生命形态。梭罗说:“如果把你的目光直接朝内看,就会发现在你的思想中有一千个领域尚未被发现。”我在大自然中朝外看苔藓,惭愧不已。
我开始读苔藓。苔藓不语,即使在荒漠中也能生存,即使沉睡千年也能死而复生。苔藓无根,却不畏严寒。冬天的大兴安岭,山林苍茫,河流冰结,驯鹿会在冰雪下寻得一口口绿苔,维持生存的能量;北极因地球变暖,寒冰融化,北极熊在缺少海冰助力捕食海豹的夏季,转战陆地,吞食苔藓。苔藓是个谜,它在地球上有四亿年拓荒史,经历过怎样的防御、浩劫、挣扎,从而生存和繁殖下来。
上个月,我应文友邀请回到故乡玉环,去山上看海。我们去的地方叫内山,山巅的平地开满白芨的紫兰花,波浪般延伸至山涯,山涯下便是波澜壮阔的东海。还没来得及看海,我被一幢茕茕孑立的石头屋抓住眼球。石头屋四间面,两层楼,石缝和瓦檐上长满苔藓,二楼墙体石条上雕刻着两个“喜”字,房前有两株并肩而立的高大香樟树,一对古稀老人在门庭外忙着农活。这个村已全部迁到山下,两位老人怎么还留守山上?阿姨朝我笑了笑,我忙问:“您二位怎么没有搬到山下去呀?”“孙儿们都长大了,去上学了,我们就回山上种点蔬菜,时常给他们送点过去。” 我得寸进尺:“这石条上的两个喜字是办喜事时刻上的吗?”“不是不是,这房子是俺老头子和他兄弟七十年代建造的,喜字只是添个喜气,山里有石矿,俺老头会雕凿石板,就刻好砌上。”阿姨挺热情的,我想继续与她聊天,就站在墙头把身体往墙边靠一靠,手不自觉地按在矮墙上,滑滑的感觉,原来是碰到墙头上的一方石锁。石锁已是斑驳陆离,似历尽沧桑,目之所及的立面长满青苔,青苔呈蓝绿色和靛蓝色,如千年铜锈。阿姨见我注视着石锁,又笑着说:“这是我老头年轻时练功用的,长久没练了,慢慢让苔藓给吃得不成样子了。”
石锁被苔藓吃了?我如听见海崖下的岩石被浪潮撞破的轰然巨响。
是的,苔藓为了生存,在光合作用下分泌出一种独特的液体,这种液体能化石为泥,但苔藓的生命力也会因此逐渐枯竭,枯竭的苔藓便成为孕育新生命的养分。它们在新陈代谢过程中,有不竭的生命力和令人惊叹的摧毁力。
人类岂不也如此,我们在消耗生命力的同时,也获得生命的养分,前行的力量!
声明:免责声明: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,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,与本网无关。仅供读者参考,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