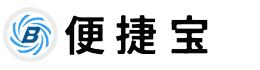


我很看重自己收藏的初版《星火集》。

上初中时,我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常提“何其芳”的名字,总是把何的职务“文学研究所所长”挂在嘴边,似乎对他有些崇拜。在我这个懵懂少年看来,大概全中国搞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,都归这个“所长”管。近50年前,“文学”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极高,高到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,那么,“所长”的厉害程度想都不用想。
后来明白,所谓“所长”,不是如今“创意写作班”导师,而是要管俞平伯、钱锺书、余冠英的领导。学界流传“何其芳的理论加钱锺书的材料”乃做学问之最高境界,真不是开玩笑,只须证诸何其芳的《红楼梦》研究,信然!
当“中国现代文学史”成为我的一门功课时,“何其芳”三字写在里头。那时教科书里,可以没有钱锺书、张爱玲、穆旦,不可不提何其芳。
1936年对何其芳来说是个里程碑:3月,《汉园集》出版,确立了他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;7月,《画梦录》出版,确立了他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。次年,首届并且是唯一一届的“大公报文艺奖金”颁给了《画梦录》(散文)。可以想象,一个大学毕业才不久的年轻人该是怎样地春风得意啊!
1938年8月,26岁的何其芳已经站在延安“鲁艺”的讲台上,并成了正宗“三八式”干部;1939年,担任文学系主任。
学术界对于何其芳“突然变成另外一种人,写出另外一种文章”的原由,有所讨论,很多文学爱好者对其抛弃“唯美-象征主义”转向拥抱“现实主义”的标志性作品的兴趣可能更大。何其芳大学同学卞之琳说过,何的“文风从他《还乡杂记》开始的渐变来了一个初步的突变。与思想内容相符,他的笔头显得开朗、尖锐、雄辩”。这个评述当然权威。不过,卞先生恐怕忽略了一件事:《还乡杂记》是何其芳把1936年9月29日至1937年6月11日所写的8篇文章编成一册寄往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。由于出版方状况频出,竟至1939年8月才出版。因此,这部作品与何抵延后的创作毫无关系。那么,真正能体现其那种“转折”的关键之作是什么?是《星火集》!
1945年初,何其芳从1938年至1944年发表的文章中选取20篇,再加上2篇未公开发表的文章,连同“后记”,裒成一集,送交重庆群益出版社;9月,《星火集》问世,初版1000册,由廖冰兄装帧。全书共4辑,第一辑收录1938年在成都从事抗日救亡文化工作的感悟,含《论工作》等7篇;第二辑收录从成都赴延安及在延安和前线的见闻,含《川陕路上杂记》等6篇;第三辑收录对生活道路和思想感受的回顾,含《一个平常的故事》等5篇;第四辑收录《关于艺术群众化的问题》等4篇论文。
《星火集》目录页
看本书目录,读者对他的文风大变已有心理准备。其实呢,如果人们不轻易被那些非诗化、非散文化的标题带偏,直接去字里行间咂味,便会深刻感觉到作者身上昔日文坛“翩翩佳公子”的气质并未“脱胎换骨”,比如,他写道:“客观的存在着的环境的限制是不能抹杀的。不过工作有着不同的种类,许多的做法,这唯一的理由是不够作为懒惰、苟安,以及东方式的个人主义之类的辩解的,因为被石头压着的树也可以生长……就比如说那个失恋的人吧,他因为失恋而到西北去,不比因为失恋而自杀,而颓废,而糊涂下去强得多吗?”至于“那悲伤的、沉郁的、绝望的旧世纪,那迷失中的叫喊和病痛中的呻吟,那黑夜,为着更勇敢地去迎接曙光,去开始新的一日的工作,我们所唱的歌应该是快活的、响亮的、阳光一样明朗的调子。这是很不同于无知的快乐和幼稚的欢欣的。这是由于充满了信心和希望,而且从残酷、艰辛和黑暗当中清楚地看见了美好的未来”(《论快乐》),让人清楚地看出作者出身于清华外文系和北大哲学系的印痕。
我很看重自己收藏的初版《星火集》,不光缘于土纸印刷,时代特征异常鲜明,还因为它后来多次再版,里面的文章不断被调整被修改,不复原汁原味了。不禁感叹:吾之“星火”,何其芳菲。
声明:免责声明: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,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,与本网无关。仅供读者参考,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